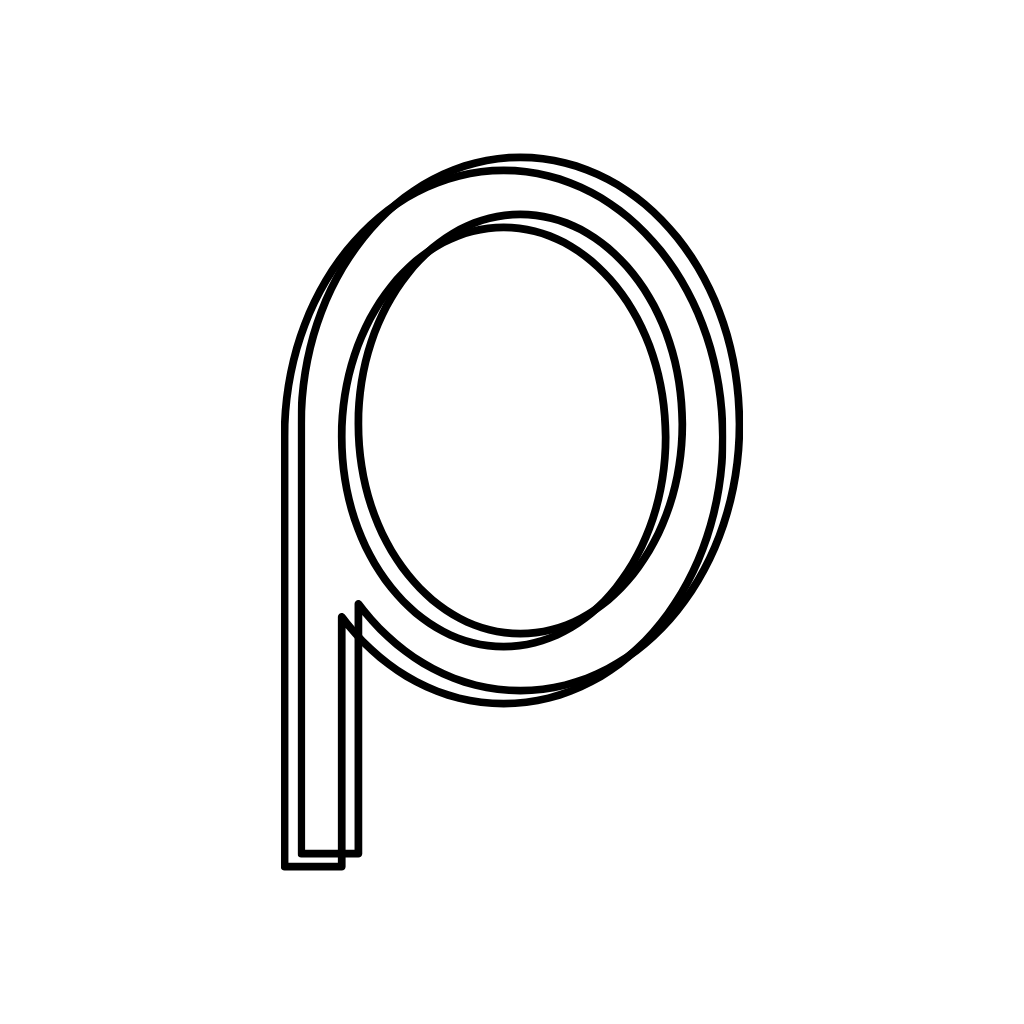修了一學期的資工系必修課 DSA(資料結構與演算法),想分享一點對台大資工系的觀察,還有一些小故事。
首先關於系名,在資工系,似乎更偏好稱呼自己的系名為資訊系,或許是半玩笑半認真的,在一學期後已經相當習慣資訊系的名稱。
接著由外而內來探究,踏入資工系館,映入眼簾的同學們,大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男生,這樣極端的男女比,也就衍生了一些在這裡司空見慣的狀況。
舉例來說某次進行了資料結構、演算法為主題的 Kahoot 活動,大家填上學號進入遊戲開始競賽,其中某個學號的同學成績出彩獨佔鰲頭,助教便很自然的誇讚「學弟不錯喔」。
第一次聽到時我覺得這樣似乎不太合適,後續助教又如此稱讚了數次,可以看出助教全然是不帶著任何惡意的,他只是不明白、或是自小到大生長的環境並沒有這樣的觀念或想法。
遊戲結束後的 Feedback 時間,有女同學在當下匿名反應「為什麼是學弟,也可以是學妹啊?」,也並沒有被多作理會,彷彿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了。
這或許只是滄海一粟,還有許多細節上的根深蒂固,我想假使是女生,遇到這些情況或許多少會有些不適應。
在這樣的環境,有時在資工系課堂上會有同學透過上課的 slido 向教授提問,如何才能交到女朋友,有種回到高中時讀男校的感覺;在上課時也時常能看見熟悉的豪情一中人 T-shirt、豪情一中人外套、豪情一中人書包,而這過去在管院時幾乎很少見過。
而向內深究,我認為資工系內部的討論極度盛行,到達驚人的程度。
舉例而言,DSA 課程為了方便大家討論,開設了專屬的 Discord 頻道,每一次的作業發布後,大量的修課同學會在頻道上提問所遇到的問題,不需多久便會有對應的神人提供解題思維,風氣相當正向。
另外一方面,資工系的大神文化也相當標誌性。
雖說大家入學時分數差不多,但許多人在高中時即先修相關課程、參與演算法競賽,或甚至部分同學讀的是數資班、科學班,在程式能力上便會有所落差,舉例來說,這學期的 DSA 就有一位高中生來修課,甚至並不清楚是透過什麼管道而來的。
而 DSA 有二十二位助教,由前一年的大神經過面試所組成,他們時常解答同學的疑難雜症,能力十分堅實,同時他們也會在作業題目裡展示出各式冷僻的資料結構或演算法,如 Skip List、Binomial Tree、Treap,脈脈相承的一屆一屆神人們,是這門課以挑戰性出名的一大原因。
DSA 上半學期的林軒田教授,是我印象深刻、甚至相當尊敬的一位老師。
林軒田教授是國內電腦科學領域的殿堂級人物,人稱「機器學習之神」、「田神」,曾被 Appier 從學校請去擔任首席資料科學顧問,就讀台大資工時每一個學期皆拿到書卷獎,研究所讀的是 MIT 的死對頭 Caltech(加州理工)。
Caltech 與 MIT 是根深蒂固的世仇,林軒田教授在上課時,跟我們分享過幾個這兩所學校間針鋒相對的故事,著實非常有趣。
舉例而言,某一年在 MIT 的開學季的新生訓練時,Caltech 的學生製作了一批印有 MIT 字樣的 T-shirt,並且帶到現場開始熱情的發放。
不知情的 MIT 新生和家長們,想到剛入學 MIT,非常興奮的便紛紛領走了這些 T-shirt 並穿上身,卻結果沒想到這些 T-shirt 的背後寫著:
“because not everybody can go to Caltech”
於是這些新生和家長們就傻愣愣的成為了 Caltech 的最佳宣傳媒介。
發生了這樣的事情,MIT 的學生們顯然嚥不下這口氣,於是在翌年他們籌劃了一場瘋狂的報復。
在 Clatech 校園裡的某一間學生宿舍前,有一座歷史悠久的大砲,是戰爭時代遺留下來的校園造景,也是獨特的校園標誌。
MIT 的學生們經過策劃,挑中了這樣的目標物,從東岸暗中搭乘飛機來到加州,巧妙的偽裝成了維修公司一類的人員,成功騙過了校門口的守衛,最後竟然把那門大砲裝上貨櫃車,直接運回 MIT 去了。
諸如此類的故事很多,也是在課堂之外很好的收穫,而林軒田教授除了教學上十分用心外,也時常針對學生的建議做溝通、檢討,其看待事情的格局我認為非常值得學習。
談回來台大管院吧,管院在概念上幾乎就是一個單位、單元,對標起來,我認為在最頂尖的那一群人並不遜色於資工系或是資訊系。
從我的角度來看,管院的學生相對於資工系的優勢在於 people skill,無論是用具體且有邏輯,甚至大方的方式表達,或是與人溝通、團隊合作,再到人與人相處之間的進退拿捏,都是管理學院學生很大的價值。
然而,這些是我們在管院的課程、在 NTU、在大學教育學的來的嗎?
並不盡然,又或者說,幾乎不是,也許大多是與生俱來的人格特質天賦、以及成長背景的培養使然。
那 NTU、大學高等教育究竟可以給我們的是什麼?
技術能力,是我在尋尋覓覓後找到的答案,
That’s why I’m here。